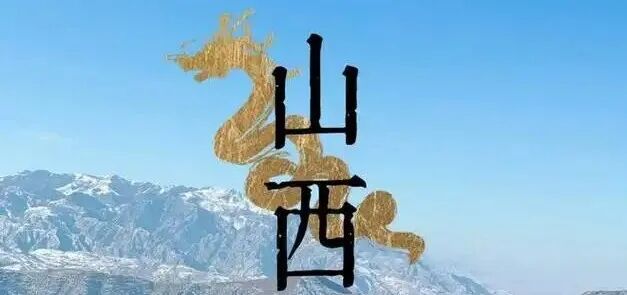
“地上五千年”的华夏摇篮---山西省。
山西是国家煤炭生产大省,从这片土地掘出的黑色黄金,几十年以来,源源不断的输向祖国各地,长期支撑着各地的能源需求,为国家、为沿海各省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挖煤必然带出很多的煤矸石,这是一种与煤伴生的固体废弃物,由于常年缺乏特别有效的处理处置办法,形成了巨量的历史堆存,且仍在源源不断的产出,山西由此在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背负了严重的煤矸石污染的包袱。全省生态环境一直受到煤矸石的严重拖累。几十年来,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懈地推动技术创新,山西省也正在一步一步地把煤矸石从“生态包袱”向“绿色财富”进行转化。

下表可以让我们看到当前山西省煤矸石的基本情况及处理处置的现状。
 长期的与煤矸石的博弈过程中,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短期化VS保护生态环境、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平衡中,对于煤矸石的处理处置,不仅不能满足于“消化、消纳”,还要追求高值化的利用和建立产业全链条的绿色发展。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煤炭及相关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煤矸石转化为高科技产品。例如,利用煤矸石作为原料,制备石油裂化催化剂,产品价值从每吨百元级别元跃升至几千元元 ;或生产用于航天、军工等领域的陶瓷/玻璃空心球 。这是一种“变废为宝”的模式,能够大幅提升煤矸石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同时,各级政府牵头,推动建设了一批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园,如朔州神电固废综合利用工业园 ,初步形成了发电、制砖、新材料等产业集群 。以太原、晋城等“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为抓手,着力推动从源头减量到末端综合再利用的全过程治理 。对于煤矸石的处理处置及综合再利用,尽管取得了一些较为显著的成效,但是全省面临的挑战依然巨大。历史的堆存量巨大、总体利用率仍然较低,后端产品的市场需求容易产生波动,严重影响消纳能力 。
长期的与煤矸石的博弈过程中,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短期化VS保护生态环境、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平衡中,对于煤矸石的处理处置,不仅不能满足于“消化、消纳”,还要追求高值化的利用和建立产业全链条的绿色发展。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煤炭及相关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煤矸石转化为高科技产品。例如,利用煤矸石作为原料,制备石油裂化催化剂,产品价值从每吨百元级别元跃升至几千元元 ;或生产用于航天、军工等领域的陶瓷/玻璃空心球 。这是一种“变废为宝”的模式,能够大幅提升煤矸石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同时,各级政府牵头,推动建设了一批固废综合利用产业园,如朔州神电固废综合利用工业园 ,初步形成了发电、制砖、新材料等产业集群 。以太原、晋城等“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为抓手,着力推动从源头减量到末端综合再利用的全过程治理 。对于煤矸石的处理处置及综合再利用,尽管取得了一些较为显著的成效,但是全省面临的挑战依然巨大。历史的堆存量巨大、总体利用率仍然较低,后端产品的市场需求容易产生波动,严重影响消纳能力 。
当前,在煤矸石综合利用领域,山西省正在慢慢超越简单堆填的阶段,努力形成多层次、多路径的利用格局。
第一、 大规模消纳为主的利用
面对煤矸石庞大的产生量以及历史堆存量,这是目前消纳量最大、且相对普遍的方式,主要目标就是希望快速消纳处理巨量的煤矸石。1、发电和供热:对于热值较高的煤矸石(如1200-1500大卡/千克),进行循环流化床发电。一个中型的矸石电厂每年可消耗上百万吨煤矸石。但缺点是,能源转化效率相对较低,且仍然需要处理燃烧后的灰渣。2、生产建材:制砖:技术成熟,用煤矸石可以完全替代粘土,节约了土地资源,又利用矸石自身的热量实现“内燃烧砖”,有着较好的节能效果。在一些地方成为消纳矸石的重要途径。但销路的好坏会严重影响消纳的数量。生产水泥掺合料:将煤矸石煅烧后作为水泥的活性混合材料,技术成熟,但受到水泥行业自身的制约。3、井下充填:这是从源头解决问题的理念,实现“矸石不转移”。其中一种做法,将掘进产生的煤矸石直接破碎后,通过专业设备回填到采空区,既能处理固废,又能控制地表沉陷,实现“以废治害”。但技术成本和适用条件有一定限制。
第二、高附加值利用
其目的在于“点石成金”,提升后续产品的经济效益、扩大销售半径。1、提取有价元素:某些煤矸石富集铝、硅以及稀有元素,可以用于制备化工产品,如聚合氯化铝(净水剂)、白炭黑、分子筛等。但这要求矸石成分相对稳定且有特定;目前多为技术示范,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2、生产新材料:利用煤矸石制备陶瓷颗粒、耐火材料、土壤改良剂等。这些领域附加值高,但技术门槛也高、市场容量却相对有限,实践已经证明,难以消化巨量矸石。
第三、生态修复与土地复垦
对历史遗留的矸石山进行综合治理,包括灭火、边坡稳定、覆土绿化,最终恢复为耕地、林地或公园。这不仅是处理历史欠账,也可改善了矿区生态环境。 在取得很大的进步的同时,要最终实现煤矸石的“吃干榨净”、化害为宝,全省各地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挑战,总之,理想丰满,现实骨感!1. 资源禀赋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首先,煤矸石是“劣质资源”。煤矸石本身是采煤的伴生物,其成分复杂、波动大,热值低、含硫量高、灰分高(一个矿一个样、一个洗煤厂一个样)。这决定了它天生是一种“劣质”资源,加工利用的处理环节多、成本高、效益低。其次,煤矸石利用后的产品市场竞争力弱。煤矸石制砖的成本通常高于传统粘土砖;(彻底杜绝生产传统粘土砖?!)煤矸石发电的上网电价需要政策扶持才能与燃煤电厂竞争(算不算新能源发电?!)。一旦外部市场变化或政策支持力度减弱,综合利用项目很容易陷入“亏本不经济”的困境。2. 技术始终有瓶颈,产业链始终有短板首先,应对煤矸石的多数技术“不通用”。众所周知,不同矿区、甚至同一矿区不同层的煤矸石成分差异巨大。一种在一地成功应用的技术方案往往难以简单复制,需要针对性地进行技术改造,这就增加了研发和投资成本。其次,高值化利用往往“叫好不叫座”:从煤矸石当中提取有价元素、生产新材料等技术,虽然论证起来都是前景广阔,但当下普遍存在技术不成熟、工艺流程长、投资巨大、市场需求不稳定等问题,难以实现利用煤矸石的规模化、产业化,事实上无法承担起消化数以千万吨、亿吨计矸石的重任,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的改善出力难以直观显现。3. 历史包袱巨大而且区域分布不平衡首先历史存量巨大:各种各样的合规处理处置方式、五花八门的综合再利用的项目,在每年数千万吨的新增矸石尚难有所表现,再面对十亿吨级的历史堆存,更加显得杯水车薪。大量存在的老旧矸石山,内部成分不明、多数含有有害物质,治理的难度和成本极高。其次,省内各地区分布不均:煤矸石产生于矿区,但综合利用产品的市场往往在城市和工业区。长距离运输,对于低价值的煤矸石或初级产品(如矸石砖)物流成本高昂,这就严重制约了消纳范围,事实上造成了“产处不用,用处不产”的矛盾。4. 政府的政策与市场的协同难题首先,煤矸石等大宗固废对于政策的依赖性极强:当前的综合利用产业严重依赖税费减免、发电补贴、绿色采购等政策。政策的任何波动都可以对整个行业造成巨大冲击。其次,“谁产生谁治理”的责任实际上难以真正落实:虽然法律有规定,但很多煤炭企业(尤其是经营困难的企业)治理投入严重不足,缺乏内生动力,往往选择成本最低的堆存方式,甚至不合规转移,继而导致新的环境问题。(即便看似合规的填埋场,也是环境漏洞百出)

最后,我们盼望山西省继续在在煤矸石综合利用上朝着“大规模消纳为基础,生态修复为保障,高值化利用为方向” 的多路径格局去发展。面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面对巨量的、低品质的煤矸石与市场化、高效益的处理方式之间难以匹配的根本困境,真正的破局之道,还是在于技术、政策和商业模式的协同创新:一方面通过政策强制和激励“逼”和“拉”企业进行利用;另一方面,更要通过核心技术突破,真正降低成本和提升产品价值,让综合利用从“任务”转变为企业自觉的“经济”选择。